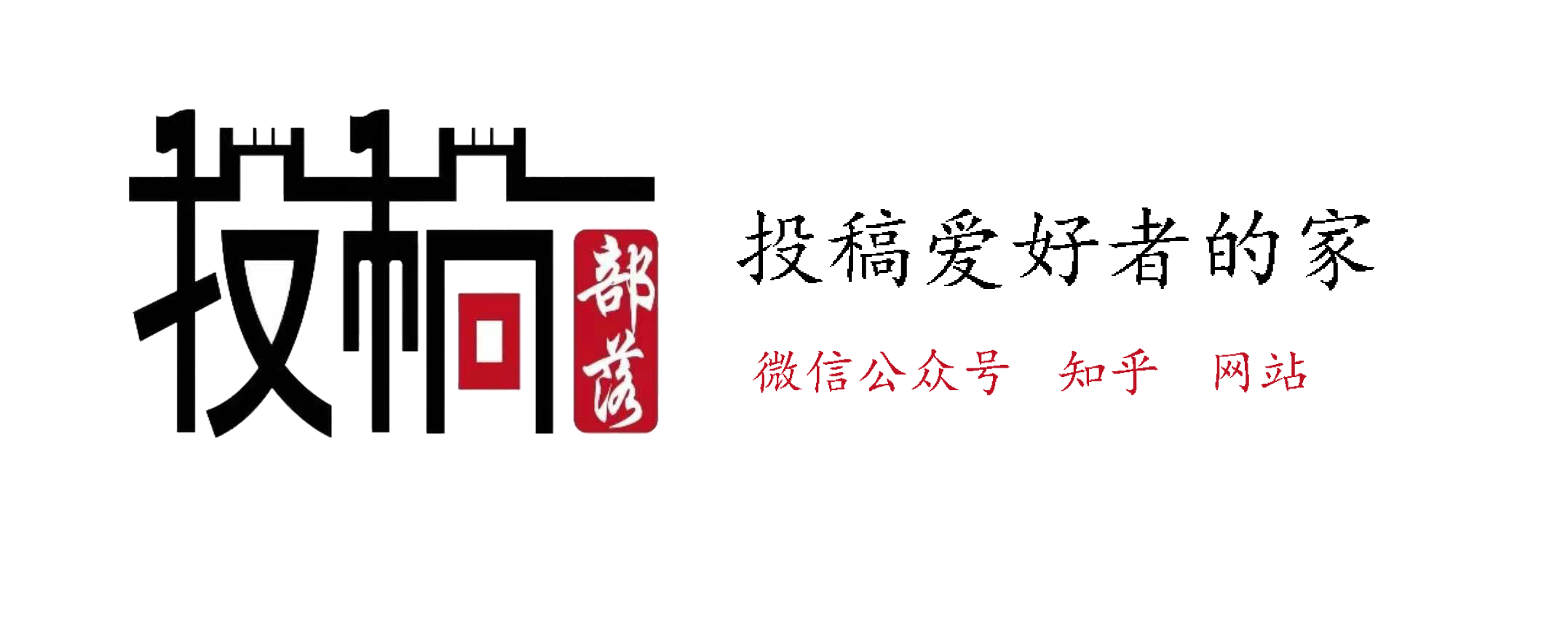家乡的老屋
按照农村的习俗,儿女成家了是要单独成家立户的。爷爷奶奶也没什么留给父亲,就把老宅的地基留给了父亲,自己另外选了一个地方带着其它叔叔们分开住了,我的印象中家里曾经是有一头牛的,应该也是爷爷分给父亲的。在原来老宅的地基上,父亲重新建了房子,算是和母亲安有了个窝,从此这老屋也就成了一直伴随我们小时候成长的家。
老屋的位置是不错的,门前有块不大的平地当做晒场(本地的话叫“稻冲”),同时也是后面几户人家以及爷爷奶奶搬家后必经的道路。晒场挨着就是堰塘,再远处便是河道,跨过河道便是一条横冲,全是水田。左邻右舍都有住家户,都是挨着住了几辈子的人。平时父母亲邻里关系也处的算是和睦,但从母亲的嘴里多少能感受到,邻里之间的那种攀比心思也是存在的。
老屋是一正一偏的土屋,砌墙用的泥砖是父母亲在田里用锹一块一块铲出来的,墙面抹的是泥灰,地面也是夯实了的泥土,盖房的梁和木檩条是从萧儿山砍的树。房子不大,但结构还算方正,中间为堂屋,面积最大,也是整间房子里地面最平整的地方。堂屋最里面靠着山墙以前是放着一个木制的大斗柜,我记得应该是外公帮忙打了用来装谷子的,后来因为老鼠太多,把这个斗柜啃的到处都是窟窿,父亲索性就把它拆了用砖砌了一个正方体的“仓库”,这也是家里唯一一处用砖搭建的设施。谷仓旁边堆满了平时农活时用到的锄头、洋锹、犁头和打农药用的喷雾器等等,还有父亲平时骑的自行车和搞自行车修理的一些工具。母亲总是抱怨父亲把家里东西堆放得乱起八糟,一点都不知道收拾。进入堂屋的左手边,摆放的是母亲时常用到的石磨。母亲需要用磨做的两样东西我一直特别喜欢,一个是豆皮儿,另一个是用麦芽糖熬制切割而成的米糖。为此,我小时候也没少帮她推磨。因为是手工推,所以必须一个人推,一个人往石磨里面灌浸泡好的大米或麦子,并且两个人还必须保持默契,控制好节奏和灌的量。磨推快了,会磨出沙子溶入浆中,吃起来磕牙齿,磨推慢了,则磨出来的米浆又太粗不细腻,吃起来影响口感。说起豆皮儿,其实应该叫米皮儿,哥哥和我肯定都是特别怀念的,他主要是吃的多,我不仅喜欢吃,而且帮着做的时候也多,这也算是我值得骄傲的一点。磨一次的豆皮儿晒干后可以吃一整年,母亲知道我们喜欢吃,我们每次读书放假回家,她都会煮上一锅,炒点肉码子,放上两个荷包蛋,给我们满满地盛一大碗。熬米糖其实不是母亲的强项,除了需要熬糖用的麦芽浆外,更关键的是熬制时的火候把握,火大了的话麦芽糖就焦了会发苦,火小了则麦芽糖又化不开,无法和炒的爆米花儿均匀地粘连在一起。所以一般这个时候都会请爷爷来帮忙,他是熬糖的老把式,每到过年都要做。后来,母亲一个人在家也没个帮手,就慢慢地不做了。堂屋的右手边靠着偏屋,离灶屋近,靠墙放着一张木圆桌和几把木头椅子,请客或者吃团年饭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堂屋吃饭,灶屋太小人一多就坐不下了,另外也是出于对客人的尊敬。
紧靠着堂屋的左侧为两个卧室,靠里面的卧室大一些,是父母亲睡的地方,房间里放着两张床,中间是他们结婚时的嫁妆,一面带镜子的梳妆台,其实我基本没看过母亲化过妆,最多也就是冬天抹点防裂口的防冻霜,父亲也从没给她买过什么化妆品和首饰。我的印象中台子上应该还有两个百灵鸟形状的陶瓷插花瓶,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我给败坏了。母亲床的后面放着一个木衣柜,衣柜不大,衣服都是母亲叠好放进去的,柜子也是他们结婚外公帮忙打的,母亲经常把手头上的零钱放在柜子的最底层。衣柜的旁边是米缸和油缸,每次打的新米和菜籽油都会装在这两个缸里作为日常食用。母亲弄饭时,我除了帮忙烧火外,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负责拿着空油罐去油缸里打油。我在母亲的床上睡得时候多,她喜欢干净,每次都把床单和被子铺的齐齐整整的。并排着的父亲的床则要乱很多,父亲喜欢什么都往床上放,乱七八糟的衣服堆在一起,为此母亲说过父亲很多次,现在也还经常念叨着。按照道理父亲不该是这么不讲究的人,他教导我们以军人作风来约束自己,自己却收拾的乱七八糟。父亲的床尾也有一个木柜子,基本都是放一些吃的东西,也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翻的宝藏盒。晒干的豆皮儿、切好的米糖、过年买的瓜子、糖果等通通都藏在这个柜子里,等家里来客了一点一点拿出来吃。这个卧室虽然大但是没有窗户,晒不到太阳,里面一直都阴阴沉沉的。而且屋顶也漏雨,一到下雨的时候母亲就会拿着脸盆放在蚊帐架子上接雨,免得把床上打湿。我和哥哥睡在靠外面的卧室。这间卧室开始也没有床,而且窗户也很小,后来父亲请木匠打了一个绷子床,把窗户也换成了一个大的木窗户,但因为没钱装玻璃,窗户就一直用育棉苗的塑料薄膜遮着,一值到大学毕业重新砌房,我都记得没换过。床头还是放着一张带抽屉的长木桌,上面放着家里唯一值钱的电器-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母亲并不是特别喜欢看电视,因此大多数时间只有父亲一个人看,或者我们一家人聚齐的时候才看。尤其到了大年三十,一家人就守着这个电视一起守夜,那天我会把电视机直接搬到灶屋的火坑旁边,大家一边烤火一边看晚会,值到凌晨守岁放完鞭炮才去睡觉。这间卧室也不大,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后就没剩下多少空间了,其他都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父亲修车补鞋的配件、工具,还有我们上学不断累计成堆的课本。
堂屋的右侧为偏屋,主要为厨房和猪栏,以及猪栏后面一个用油毛毡遮盖着的厕所。对于农村的人来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吃喝拉撒,所以一家人在偏屋呆的时间是最长的,我对这地方的印象也就特别深。厨房(本地的话叫“灶屋”)的窗户也是在打床的时候换了的,换了后厨房的光线好了很多,但冬天时最遭罪了,呼啦啦的老北风从窗子塑料薄膜的缝隙里钻进来,整个灶屋冷的如同冰窖一样。灶屋的地面非常不平,每次吃饭摆桌子,我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一个把桌子四条腿都能放稳的地方。灶台就是靠窗搭建的,农村里的灶台基本上都是放两口锅,一口锅平常做饭用,另一口锅煮猪食用,或者等到过年炖猪脑壳。灶台上并没有修烟囱,每次一弄饭碰到烧柴不干,满灶屋都是烟熏火燎的,呛得人眼泪鼻涕直流。做饭基本上都是母亲的事,父亲是帮不上半点忙的。小时候吃肉的机会不多,基本上只有“双抢”最忙的时候或者过年的时候才吃得到。我们生日的时候,母亲才会给我们煮两个荷包蛋解解馋,蛋是家里鸡生的,不花钱。平时的话,基本上是家里的菜园里什么菜出来了就吃什么菜,春夏吃辣椒茄子黄瓜,秋冬吃冬瓜萝卜白菜,基本上就这几样菜换来换去。虽然谈不上什么丰富营养,但也算是应季健康。碗柜、水缸、猪食缸沿着灶台靠墙一字排开,五味杂陈。父母亲都是很节约的人,吃不完的剩菜剩菜是不会直接倒进猪食缸喂猪的,会用碗扣着放在碗柜里等下一顿再热了吃。哥哥比我更喜欢吃糖,夏天的时候,母亲就会用煮饭剩下来的锅巴给我们煮一大锅粥一碗一碗盛好放在碗柜里,等我们放学回来了自己吃。光喝粥是没什么味道的,有时候没有菜,哥哥就使劲地往粥里放黑糖,这样他一次可以吃两三碗,后来搞成习惯了,走到哪里都要喊着喝糖粥,导致现在老一辈的人都还记得,只要一提起他就说起这件事。挑水基本上都是父亲的事儿,家里有一担木水桶,挑一担也有几十斤,基本上三到四担就把水缸装满了,水是门口堰塘里的,还算干净。母亲力气小,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就用小的塑料桶挑,吃多少挑多少。后来,家家户户开始埋管子从堰塘里面用泵抽水,挑水吃的日子就基本上看不到了。这个水缸算是家里最大的器具,从我记事起就一直在用,怎么也用不坏。水缸旁边就是放猪食的猪食缸,母亲在外扯的并剁碎了的猪草,单独熬的猪食、做饭洗锅时的洗锅水,馊了的饭菜等等,都会在倒进里面。小时候我放学回家,第一件事通常就是喂猪食。首先用瓢在猪食缸里搅拌一下,把猪草和熬的猪食混匀,然后舀两三瓢到猪食桶里,舀的时候要不能太稀也不能太干,太稀了猪吃不饱,太干了猪不吃,再把猪食桶提到猪栏旁边抓上几把糠,最后才能倒进猪槽里。和人的三餐一样,必须定点给猪喂上猪食,不然猪饿急了会翻栏在家里到处跑,猪也长不大。
老家的冬天很冷,几尺厚的雪压着根本出不了门。因为是偏屋,呆在屋里和外面基本差不多,但我们依然喜欢呆在这里。为了保暖,农村家家户户到了冬月间就开始搭火坑,几块土砖靠着墙围成一个框,里面就开始烧柴,有点类似北方的炕,但比炕又更实用一些。除了大家围坐在一起烤火之外,还可以在火坑里放个铁架子,把锅直接放在火坑里烧水弄饭,过年杀了的猪鱼肉还可以挂在火坑上面烟熏着做腊肉腊鱼。我们家的火坑也不例外,也是搭在灶屋里的,靠着猪栏的这堵墙。每次搭火坑,母亲都将灶屋打扫得干干净净,把从萧儿山砍回来的树木锯成一节节的柴禾堆一垛在旁边,方便随时烧添。久而久之,搭火坑成为了一种仪式,意味着快过年了,我们也快回家了。火坑,是一家人在一起交流最多的地方,我们都围坐在火坑边上,既可以各忙各的事,也可以你一言我一语地互相搭话。母亲做饭也不再是一个人默默地弄,父亲也可以将他的家伙什摆在旁边剖蔑打竹篮,我们也能见缝插针地给他们打下手,没事即使干坐着也热火的很。因为火坑和猪栏只是一墙之隔,猪也喜欢暖和,每次都是紧贴着这面墙睡,我们坐在这边都能听到它的呼噜声。
偏屋在猪栏的这一节因为有根横梁被檩条压断了,父亲一直都没管,每次喂猪食或者路过上厕所,我都一直担心偏屋有垮塌的风险。可是也奇怪,值到大学毕业家里拆屋重建偏屋也没垮。猪栏被隔开成两个,很小的时候家里养过两头猪,后来粮食不够就只养一头了,另一边也就一直空着放粪筐、竹篮等杂物。平常猪基本都是被圈在栏里,除了每日定时的喂食外,每隔一段时间还要清洗猪栏,先把猪粪铲起来挑出去倒在田里,再用水把猪栏冲刷干净。到了炎热的夏天,还需要把猪用绳子套着牵到外面晒场边上的枣树下下透气,不然容易生病。母亲干活是个精细的人,每次扯回来的猪草都是细嫩的棒头草,杂叶子在剁的时候都会挑出来丢给鸡吃,猪草剁得极为细碎,生怕猪吃了噎着。我就因为每次扯回来的猪草不合格而被她骂过好多次。可能是猪肉的精贵吧,那时候都不时兴喂饲料,即使大家都知道吃饲料的猪长得快,母亲也舍不得花钱去买饲料喂。一年到头,全家桌上的肉菜都指望在这头猪上,可是无论母亲怎么精心喂养,一头猪杀下来也才一百来斤。一到冬月间,家家户户都开始准备杀年猪,杀猪这一天很重要,日子必须要提前选好,同时要请当地最有名的杀猪匠,这段时间杀猪的特别多,杀猪匠的生意也特别好,必须要提前预约。杀猪,也确实是一门技术,必须一刀致命,而且杀完要有足够的肺活量把猪吹胀起来,这样才好烫猪毛和后续的切割,切割的时候还必须按照猪身上的结构来,一头猪杀下来无论大小该多少块就是多少块,一块不能多也一块不能少。杀完猪东家是要招待吃杀猪饭的,每到这天母亲都会弄上一桌子猪肉菜,猪血、猪大肠、猪心肺等等。杀猪匠们吃完饭,拎上一块猪板油就当做今天的酬劳了。对于自家人来说,猪肉可不会这么敞开吃的。母亲会把所有的猪肉都用盐抹一遍放在缸里,一点一点地割着吃。需要过年吃的猪脑壳、猪蹄等也都先挂在火坑里提前熏着。这样断断续续地,一直要吃到来年冬月间。因为水田少,种的粮食不够一家人吃,慢慢母亲也不养猪了,猪栏也就一直空置在这里,没做其它用处。穿过猪栏,也就走出土屋的主体结构了,出了后门就是用油毛毡搭得茅厕。与其说是茅厕,其实就是一个棚,几根树木靠在后面的山墙上,然后用油毛毡一遮就成了。一到夏天,苍蝇、蛆虫爬的到处都是,连找个下脚的地方都难,冬天就不用说了,呼呼地北风直接往油毛毡里钻,让人冻得直哆嗦,多呆一秒钟都是煎熬。茅厕本该用土砖砌墙围起来的,母亲也说过很多遍,但是父亲一直没弄,可能这是这个家庭最不重要的事情吧。
老屋后面,是一片茂密的楠竹林,父母亲也基本没打理过,因为竹根盘结的到处都是,母亲恨不得全部挖了。我们每年寒假回家必须要参加的劳动之一便是要把围着屋檐的阳沟都挖通一遍,一则方便屋檐留下来的雨水沿着阳沟排到屋前的堰塘里,二则把发过来的竹根挖断避免竹子长到屋里。也不知为何这片竹林每年都长得越发茂盛,年年挖年年长,让我记忆尤为深刻的是有一年,父母亲实在凑不到我们上学的学费,把这片竹林的竹子砍卖了才凑齐。每年到春上,到处都是竹笋,母亲也不稀罕,只是偶尔挖两根做菜吃。
分家后,父母亲也从村上分了些田地,但因为单家独户人口少,分到的田地也就少,而且因为是后面分的,也不成块,这里几分那里几分,除了门口靠近堰塘有一块较完整的水田外,其它几乎都是旱地,而且也远,母亲为此很是不满埋怨了很多次,然而也无济于事。老屋的这点田地一年种下来只够一家四口人的基本生活,不得已父亲只好去外面揽活供我们读书,随着我们读书跑得越来越远,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少。成家后,连每年的春节一家人也不一定能聚在一起了,自然而然回家的次数变得更加稀少。老屋我们在毕业后就被拆掉了,一家人仍选择在老屋的地基上建了新屋。然而我对家乡的老屋印象却越来越深,伴随着长期在外对父母亲的挂念,内心深处对于在这间土屋里发生的点点滴滴,记得愈加清晰。